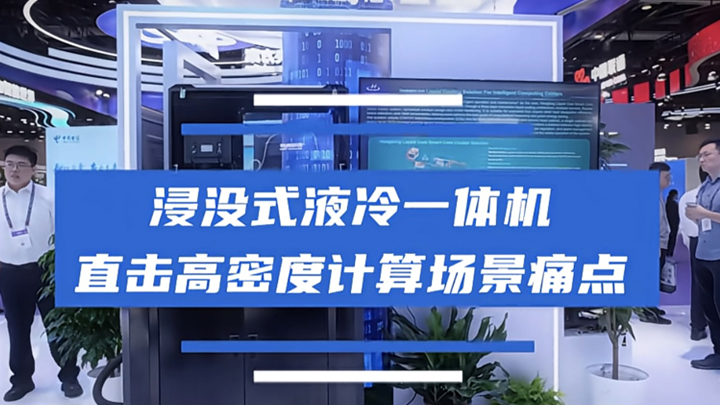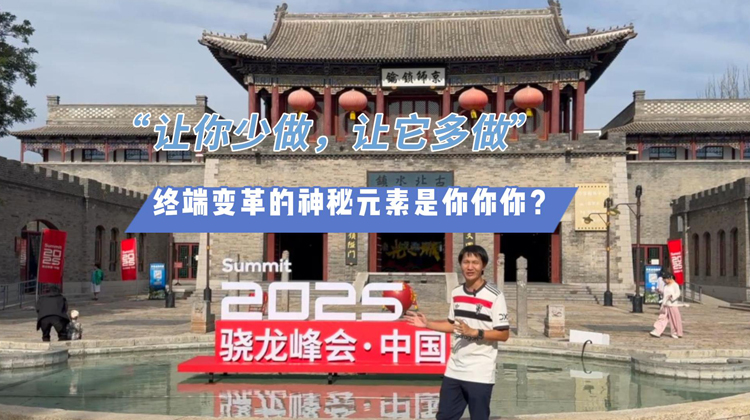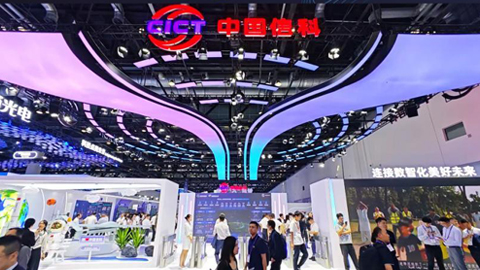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再度将全球目光聚焦超导领域,美国科学家约翰·克拉克、米歇尔·H·德沃雷与约翰·M·马蒂尼斯,凭借在超导电路中观测到宏观量子隧穿效应与能量量子化现象的开创性成果摘得奖项。
该团队通过构建嵌入约瑟夫森结的超导电路,首次在毫米级宏观系统中证实:大量超导电子形成的“库珀对”可协同展现量子隧穿特性——能从“零电压超导电流态”隧穿至可测量电压的非超导态,且能量变化严格遵循量子化规律。这一发现颠覆“量子现象仅存于微观世界”的认知,被学界称为“可触摸的薛定谔猫”实验,既深化量子与宏观材料结合的认知,更从原理上为超导量子器件实用化铺路。
百年诺奖筑基:超导科研的关键里程碑
超导是近一百年凝聚态物理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其发展进程始终与诺贝尔奖紧密相伴。百年间,超导领域共7次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涉及16位科学家,每一次诺奖成果都标志着超导科研的核心突破。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海克·卡末林·昂内斯在液氦环境中发现汞的超导特性,1913年凭此首获诺奖,开启低温超导研究序幕;1972年,BCS理论揭示低温下电子“库珀对”导电机制,为超导原理奠定理论基础;1973年,“约瑟夫森效应”预测超导体夹绝缘层的导电特性,成为超导器件研发的核心依据。
1986年,镧钡铜氧陶瓷将超导临界温度提升至液氮温区(35K),大幅降低制冷成本,研究者于1987年获奖,打破低温应用限制;2003年,超导理论体系完善,为材料改性与设备设计提供统一指导;2025年诺奖则标志超导进入“实用化量子时代”——上世纪80年代,克拉克团队构建含约瑟夫森结的超导电路,证实毫米级宏观系统的量子特性,后续马蒂尼斯将其用于量子计算,2019年“悬铃木”处理器实现“量子优越性”,为超导技术开辟新赛道。
从实验室到产业前夜:超导技术的转化鸿沟
科研突破为超导产业化奠定基础,但从实验室到规模化应用仍需跨越多重障碍。1987年高温超导材料取得突破后,全球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始探索商用路径;2003年理论体系的完善进一步扫清了技术障碍,但产业化仍面临三大核心难题:其一,材料稳定性不足,早期高温超导带材(如镧钡铜氧陶瓷)在低温环境与机械弯曲条件下性能衰减较快,难以满足工业场景长期稳定运行的需求;其二,设备适配性差,超导磁体等核心设备与现有工业生产线兼容性较低,需对生产流程进行系统性重构;其三,成本居高不下,早期单件核心超导设备(如超导磁体)制造成本高达数十万元人民币,远高于传统铜导线或低温超导设备的综合成本。
这些问题导致2003年后的近二十年间,多数企业的超导产品长期停留在小批量试制阶段,应用场景局限于科研院所的实验装置,难以进入真正的工业市场,行业亟待具备技术整合能力与规模化生产经验的“破局者”。
破局与增长:超导产业化的实践与未来
面对高温超导产业化进程中的核心技术挑战,联创光电核心参股公司联创超导依托第二代高温超导的材料基础与理论支撑,通过系统性技术创新成为首个突破高温超导规模化商用的“破局者”——其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成功攻克第二代高温超导材料在产业化应用中面临的设备兼容性、成本控制等多项关键难题,推动高温超导磁体及设备从实验室小批量试制迈向规模化量产,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高温超导技术的工程化落地。
目前,联创超导的商用实践已深度融入多个战略领域:金属加工领域,全球首台兆瓦级高温超导感应加热装置顺利投产;新能源材料制造方面,高温超导磁控硅单晶生长装备获得合作客户的批量升级改造订单;在可控核聚变领域,成功研制百米级超导集束缆线,中标多个超导线圈项目,有力推动聚变装置向紧凑化、低成本方向发展;商业航天领域,斩获资阳商业航天发射技术研究院1960万元超导磁体订单,为电磁弹射技术发展提供支撑。这些实践精准对接核心应用场景,以实际成果印证了其作为“破局者”打通技术验证到产业应用通道的关键作用,与全球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超导产业正进入高速增长通道。据预测,2030年全球超导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53.9%。在诺奖理论的持续转化与技术迭代推动下,联创超导的成功实践不仅为行业树立了规模化商用的标杆,更通过技术突破与市场验证加速了超导技术在能源、制造、航天等战略领域的融合应用。这一“零电阻奇迹”不仅将重塑产业格局,更有望为全球能源革命、量子科技突破注入核心动力,推动人类社会进步。